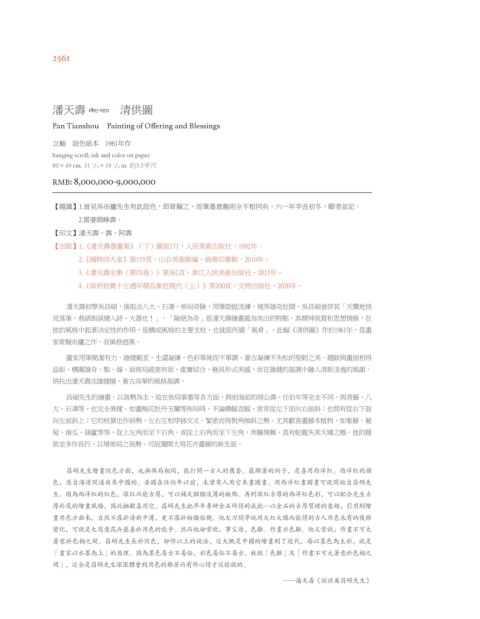Page 248 - 中国书画夜场
P. 248
2561
潘天壽 1897-1971 清供圖
Pan Tianshou Painting of Offering and Blessings
立軸 設色紙本 1961年作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
1
80×49 cm. 31 /2×19 /4 in. 约3.5平尺
RMB: 8,000,000-9,000,000
【題識】1.曾見吳缶廬先生有此設色,即背擬之,而筆墨意趣則全不相同矣。六一年辛丑初冬,頤者並記。
2.雷婆頭峰壽。
【印文】潘天壽、壽、阿壽
【出版】1.《潘天壽書畫集》(下)圖版171,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
2.《國粹四大家》第155頁,山右美術館編,商務印書館,2010年。
3.《潘天壽全集(第四卷)》第361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
4.《保利拍賣十五週年精品集近現代(上)》第200頁,文物出版社,2020年。
潘天壽初學吳昌碩,後取法八大、石濤,佈局奇險,用筆勁挺洗練,境界雄奇壯闊。吳昌碩曾評其「天驚地怪
見落筆,巷語街談總入詩,大器也!」。「險絕為奇」是潘天壽繪畫最為突出的特點。其精神氣質和思想情操,在
他的風格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構成風格的主要支柱,也就是所謂「風骨」。此幅《清供圖》作於1961年,是畫
家背擬缶廬之作,而風格迥異。
畫家用筆簡潔有力、雄健剛直、生澀凝練,色彩單純而不單調,蒼古凝練不失松的堅韌之美。題跋與畫面相得
益彰,構圖雄奇。點、線、面佈局疏密有致,虛實結合,極具形式美感,而在雄健的基調中融入清新淡逸的風韻。
烘托出潘天壽沈雄健撥,蒼古高華的風格基調。
昌碩先生的繪畫,以氣勢為主,故在佈局筆墨等各方面,與前海派的胡公壽、任伯年等完全不同。與青藤、八
大、石濤等,也完全異樣。如畫梅花牡丹玉蘭等佈局時,不論橫幅直幅,常常從左下面向右面斜;也間有從右下面
向左面斜上;它的枝葉也作斜勢,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緊密而得對角傾斜之勢。尤其歡喜畫藤本植物,如紫藤、葡
萄、南瓜、葫蘆等等,從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從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騰飛舞,真有蛇龍失其夭矯之概。他的題
款並多作長行,以增佈局之氣勢。可說獨開大寫花卉畫藤的新生面。
昌碩先生繪畫設色方面,也與佈局相同,能打開一古人的舊套。最顯著的例子,是喜用西洋紅。西洋紅的顏
色,原自海運開通後來中國的。吾國在任伯年以前,未曾有人用它來畫國畫,用西洋紅畫國畫可說開始自昌碩先
生。因為西洋紅的紅色,深紅而能古厚,可以補足胭脂淡薄的缺點。再則深紅古厚的西洋紅色彩,可以配合先生古
厚朴茂的繪畫風格,因此極歡喜用它。昌碩先生把早年專研金石所得的成就—以金石的古厚質樸的意趣,引用到繪
畫用色方面來,自然不落於清新平薄,更不落於粉脂俗艷。他大刀闊斧地用大紅大綠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複雜
變化,可說是大寫意花卉最善於用色的能手。然而他卻常說:事父母,色難。作畫亦色難。他又常說:作畫不可太
著意於色相之間。昌碩先生長於設色,卻作以上的說法,這大概是中國的繪畫到了近代,每以墨色為主彩,就是
「畫家以水墨為上」的原理。因為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說「色難」及「作畫不可太著意於色相之
間」,這全是昌碩先生深深體會到用色的艱苦而有所心得才這樣說的。
—潘天壽《談談吳昌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