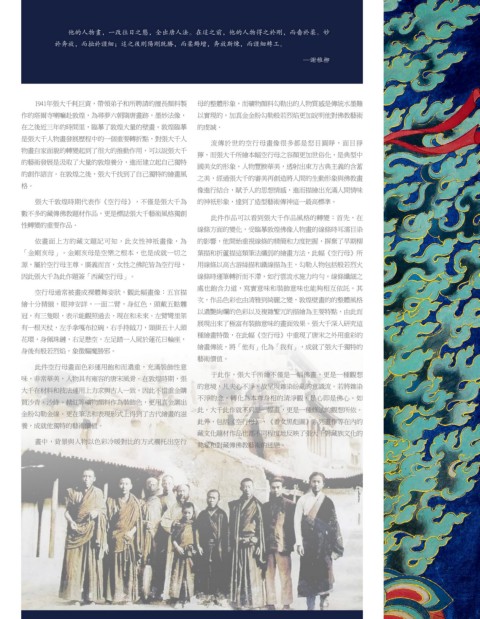Page 233 - 中国书画夜场
P. 233
他的人物畫,一改往日之態,全出唐人法。在這之前,他的人物得之於剛,而嗇於柔。妙
於奔放,而拙於謹細;這之後則陽剛既勝,而柔縟增,奔放斯煉,而謹細轉工。
—謝稚柳
1941年張大千耗巨資,帶領弟子和所聘請的擅長顏料製 母的整體形象,而礦物顏料勾勒出的人物質感是傳統水墨難
作的塔爾寺喇嘛赴敦煌,為尋夢六朝隋唐畫跡,墨妙法像, 以實現的,加真金金粉勾勒般若烈焰更加說明他對佛教藝術
在之後近三年的時間里,臨摹了敦煌大量的壁畫。敦煌臨摹 的虔誠.
是張大千人物畫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對張大千人
流傳於世的空行母畫像很多都是怒目圓睜,面目猙
物畫自家面貌的轉變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張大千
獰,而張大千所繪本幅空行母之容顏更加世俗化,是典型中
的藝術發展是汲取了大量的敦煌養分,進而建立起自己獨特
國美女的形象,人物豐腴華美,透射出東方古典主義的含蓄
的創作語言。在敦煌之後,張大千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繪畫風
之美,經過張大千的審美再創造將人間的生動形象與佛教畫
格。
像進行結合,賦予人的思想情感,進而描繪出充滿人間情味
張大千敦煌時期代表作《空行母》,不僅是張大千為 的神祇形象,達到了造型藝術傳神這一最高標準。
數不多的藏傳佛教題材作品,更是標誌張大千藝術風格獨創
此件作品可以看到張大千作品風格的轉變:首先,在
性轉變的重要作品.
線條方面的變化,受臨摹敦煌佛像人物畫的線條時耳濡目染
依畫面上方的藏文題記可知,此女性神祇畫像,為 的影響,他開始重視線條的精簡和力度把握,摒棄了早期柳
「金剛亥母」。金剛亥母是空樂之根本,也是成就一切之 葉描和折蘆描這類筆法纖弱的繪畫方法,此幅《空行母》所
源,屬於空行母主尊。廣義而言,女性之佛陀皆為空行母, 用線條以高古游絲描和鐵線描為主,勾勒人物包括般若烈火
因此張大千為此作題簽「西藏空行母」。 線條時運筆轉折而不滯,如行雲流水施力均勻,線條纖細之
處也飽含力道,寫實意味和裝飾意味也能夠相互依託。其
空行母通常被畫成裸體舞姿狀,觀此幅畫像:五官描
次,作品色彩也由清雅到綺麗之變,敦煌壁畫的的整體風格
繪十分精緻,眼神安詳,一面二臂,身紅色,頭戴五骷髏
以濃艷絢爛的色彩以及複雜繁冗的描繪為主要特點,由此而
冠,有三隻眼,表示能觀照過去、現在和未來。左臂彎里架
展現出來了極富有裝飾意味的畫面效果。張大千深入研究這
有一根天杖,左手拿嘎布拉碗,右手持鉞刀,頸掛五十人頭
種繪畫特徵,在此幅《空行母》中重現了唐宋之外用重彩的
花環,身佩珠鏈,右足懸空,左足踏一人屍於蓮花日輪座,
繪畫傳統,將「他有」化為「我有」,成就了張大千獨特的
身後有般若烈焰,象徵驅魔勝邪。
藝術價值。
此件空行母畫面色彩運用飽和而濃重,充滿裝飾性意
于此作,張大千所繪不僅是一幅佛畫,更是一種觀想
味,非常華美,人物具有雍容的唐宋風骨.在敦煌時期,張
的意境,凡夫心不淨,故呈現雜染紛亂的意識流。若將雜染
大千在材料和技法運用上力求與古人一致,因此不惜重金購
不淨的念,轉化為本尊身相的清淨觀,是心即是佛心。如
買沙青、沙綠、赭紅等礦物顏料作為裝飾色,更用真金調出
此,大千此作就不只是一幅畫,更是一種修法的觀想所依。
金粉勾勒金線.更在筆法和表現形式上得到了古代繪畫的滋
此外,包括《空行母》、《番女黑彪圖》系列畫作等在內的
養,成就他獨特的藝術價值。
藏文化題材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張大千對藏族文化的
畫中,背景與人物以色彩冷暖對比的方式襯托出空行
熱愛和對藏傳佛教藝術的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