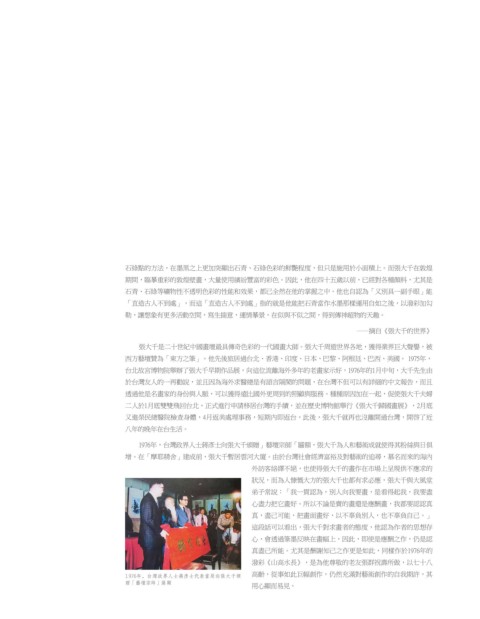Page 206 - 中国书画夜场
P. 206
石綠點的方法,在墨黑之上更加突顯出石青、石綠色彩的鮮艷程度,但只是施用於小面積上。而張大千在敦煌
期間,臨摹重彩的敦煌壁畫,大量使用繽紛豐富的彩色。因此,他在四十五歲以前,已經對各種顏料,尤其是
石青、石綠等礦物性不透明色彩的性能和效果,都已全然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也自認為「又別具一副手眼」能
「直造古人不到處」,而這「直造古人不到處」指的就是他能把石青當作水墨那樣運用自如之後,以潑彩加勾
勒,讓想象有更多活動空間,寫生揣意,運情摹景,在似與不似之間,得到傳神超物的天趣。
—摘自《張大千的世界》
張大千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最具傳奇色彩的一代國畫大師。張大千周遊世界各地,獲得業界巨大聲譽,被
西方藝壇贊為「東方之筆」。他先後旅居過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國。 1975年,
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了張大千早期作品展,向這位流離海外多年的老畫家示好,1976年的1月中旬,大千先生由
於台灣友人的一再勸說,並且因為海外求醫總是有語言隔閡的問題,在台灣不但可以有詳細的中文報告,而且
透過他是名畫家的身份與人脈,可以獲得遠比國外更周到的照顧與服務。種種原因加在一起,促使張大千夫婦
二人於1月底雙雙飛回台北,正式進行申請移居台灣的手續,並在歷史博物館舉行《張大千歸國畫展》,2月底
又進榮民總醫院檢查身體,4月返美處理事務,短期內即返台,此後,張大千就再也沒離開過台灣,開啓了近
八年的晚年在台生活。
1976年,台灣政界人士蔣彥士向張大千頒贈」藝壇宗師「匾額,張大千為人和藝術成就使得其粉絲與日俱
增。在「摩耶精舍」建成前,張大千暫居雲河大廈。由於台灣社會經濟富裕及對藝術的追尋,慕名而來的海內
外訪客絡繹不絕,也使得張大千的畫作在市場上呈現供不應求的
狀況,而為人慷慨大方的張大千也都有求必應,張大千與大風堂
弟子常說:「我一貫認為,別人向我要畫,是看得起我,我要盡
心盡力把它畫好。所以不論是賣的畫還是應酬畫,我都要認認真
真,盡己可能,把畫面畫好,以不辜負別人,也不辜負自己。」
這段話可以看出,張大千對求畫者的態度,他認為作者的思想存
心,會透過筆墨反映在畫幅上,因此,即使是應酬之作,仍是認
真盡己所能。尤其是酬謝知己之作更是如此,同樣作於1976年的
潑彩《山高水長》,是為他尊敬的老友張群祝壽所做,以七十八
1976年,台灣政界人士蔣彥士代表當局向張大千頒 高齡,從事如此巨幅創作,仍然充滿對藝術創作的自我期許,其
贈「藝壇宗師」匾額
用心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