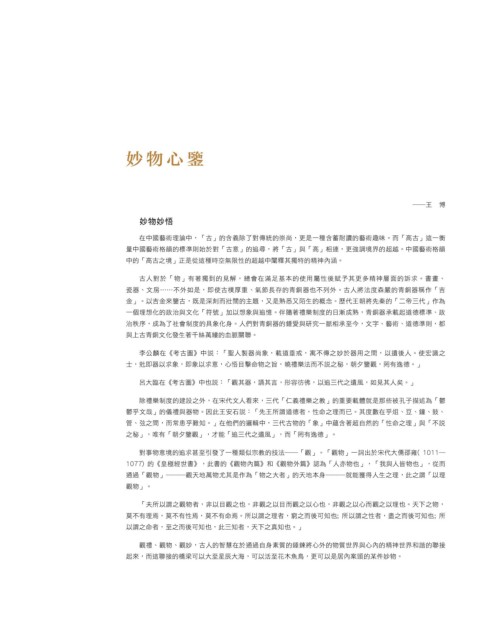Page 235 - 观古I——玉器金石文房艺术
P. 235
妙物心 鑒
—王 博
妙物妙悟
在中國藝術理論中,「古」的含義除了對傳統的崇尚,更是一種含蓄耐讀的藝術趣味。而「高古」這一衡
量中國藝術格韻的標準則始於對「古意」的追尋,將「古」與「高」相連,更強調境界的超越。中國藝術格韻
中的「高古之境」正是從這種時空無限性的超越中闡釋其獨特的精神內涵。
古人對於「物」有著獨到的見解,總會在滿足基本的使用屬性後賦予其更多精神層面的訴求。書畫、
瓷器、文房……不外如是,即使古樸厚重、氣節長存的青銅器也不列外。古人將法度森嚴的青銅器稱作「吉
金」。以吉金來鑒古,既是深刻而壯闊的主題,又是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歷代王朝將先秦的「二帝三代」作為
一個理想化的政治與文化「符號」加以想象與追憶。伴隨著禮樂制度的日漸成熟,青銅器承載起道德標準、政
治秩序,成為了社會制度的具象化身。人們對青銅器的鍾愛與研究一脈相承至今,文字、藝術、道德準則,都
與上古青銅文化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血脈關聯。
李公麟在《考古圖》中說:「聖人製器尚象,載道垂戒,寓不傳之妙於器用之間,以遺後人。使宏識之
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擊命物之旨,曉禮樂法而不說之秘,朝夕鑒觀,罔有逸德。」
呂大臨在《考古圖》中也說:「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
除禮樂制度的建設之外,在宋代文人看來,三代「仁義禮樂之教」的重要載體就是那些被孔子描述為「鬱
鬱乎文哉」的儀禮與器物。因此王安石說:「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
管、弦之間,而常患乎難知。」在他們的邏輯中,三代古物的「象」中蘊含著超自然的「性命之理」與「不說
之秘」,唯有「朝夕鑒觀」,才能「追三代之遺風」,而「罔有逸德」。
對事物意境的追求甚至引發了一種類似宗教的技法——「觀」。「觀物」一詞出於宋代大儒邵雍( 1011—
1077) 的《皇極經世書》,此書的《觀物內篇》和《觀物外篇》認為「人亦物也」,「我與人皆物也」,從而
通過「觀物」———觀天地萬物尤其是作為「物之大者」的天地本身———就能獲得人生之理,此之謂「以理
觀物」。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 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 所
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觀禮、觀物、觀妙,古人的智慧在於通過自身素質的錘鍊將心外的物質世界與心內的精神世界和諧的聯接
起來,而這聯接的橋梁可以大至星辰大海,可以活至花木魚鳥,更可以是居內案頭的某件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