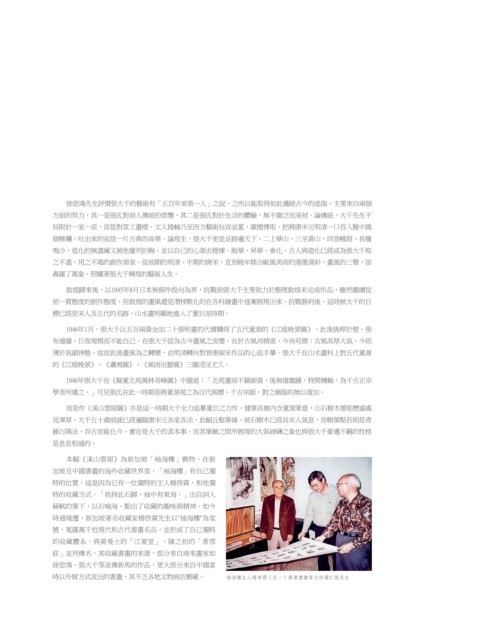Page 200 - 中国书画夜场
P. 200
徐悲鴻先生評價張大千的藝術有「五百年來第一人」之說。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邁絕古今的造詣,主要來自兩個
方面的努力,其一是張氏對前人傳統的借鑒,其二是張氏對於生活的體驗,無不廣泛而深刻。論傳統,大千先生不
局限於一家一派,而是對眾工畫壁、文人捲軸乃至西方藝術包容並蓄,廣搜博取,把將唐宋元明清一口吞入腹中搗
個稀爛,吐出來的卻是一片古典的高華。論寫生,張大千更是足跡遍天下,二上華山、三至黃山、四登峨眉、長履
鳴沙,造化的無盡藏又被他羅列於胸,並以自己的心源去提煉、脫華、昇華、參化。古人與造化已經成為張大千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從前期的明清、中期的唐宋,直到晚年糅合歐風美雨的潑墨潑彩,畫風的三變,卻
森羅了萬象,照耀著張大千輝煌的藝術人生。
敦煌歸來後,以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向為界,抗戰前張大千主要致力於整理敦煌未完成作品,雖然繼續從
前一貫態度的創作態度,但敦煌的畫風還是潛移默化的在各科繪畫中逐漸展現出來。抗戰勝利後,這時候大千的目
標已經是宋人及五代的名跡,山水畫明顯地進入了董巨派時期。
1946年1月,張大千以五百兩黃金加二十張明畫的代價購得了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圖》,此後挑桿於壁、張
布連牆,日夜規模而不能自己。在張大千認為古今畫風之流變,在於古風尚精密,今尚苟簡;古風高厚大氣,今則
薄於氣韻神態。故而此後畫風為之轉變,由明清轉向對晉唐兩宋作品的心追手摹。張大千在山水畫科上對五代董源
的《江堤晚景》、《瀟湘圖》、《風雨出蟄圖》三圖浸淫尤久。
1946年張大千在《擬董北苑萬林奇峰圖》中題道:「北苑畫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特開機軸,為千古正宗
學者所遵之。」可見張氏在此一時期是將董源視之為百代風標、千古宗師,對之佩服的無以復加。
而是作《溪山雲屋圖》亦是這一時期大千全力追摹董巨之力作。健筆長皴內含董源筆意,山石樹木蔥郁懋盛處
見渾厚。大千五十歲前就已經遍臨唐宋元各家各法,此幅丘壑筆線、坡石樹木已經具宋人氣息,而樹葉點苔則是青
藤白陽法,吞古而能化今,實在是大千的真本事。而其筆皴之間所展現的大氣磅礡之象也與張大千豪邁不羈的性格
是息息相通的。
本幅《溪山雲屋》為新加坡「袖海樓」舊物。在新
加坡及中國書畫的海外收藏世界里,「袖海樓」有自己獨
特的位置。這是因為它有一位獨特的主人楊啓霖,和他獨
特的收藏方式。「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出自詞人
蘇軾的筆下,以石喻海,點出了收藏的趣味與精神。如今
時過境遷,新加坡著名收藏家楊啓霖先生以"袖海樓"為堂
號,蒐羅萬千近現代和古代書畫名品,並形成了自己獨特
的收藏體系,與黃曼士的「江夏堂」、陳之初的「香雪
莊」並列傳名。其收藏書畫的來源,部分來自南來畫家如
徐悲鴻、張大千等流傳新馬的作品,更大部分來自中國當
時以外貿方式流出的書畫,其不乏各地文物商店舊藏。 袖海樓主人楊啓霖(左一)與書畫鑒賞大師楊仁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