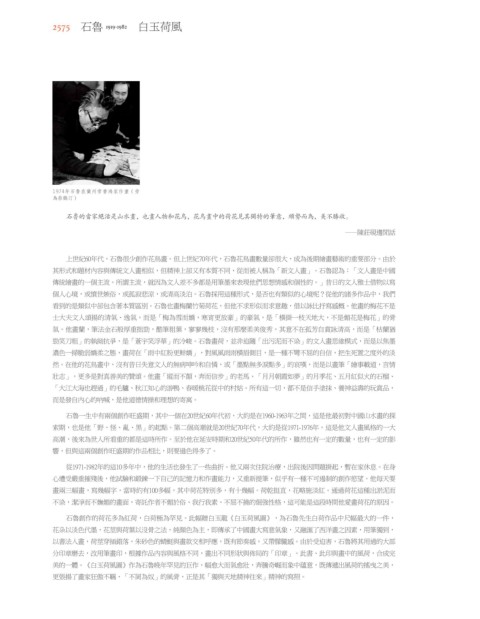Page 294 - 中国书画夜场
P. 294
2575 石魯 1919-1982 白玉荷風
1974年石魯在蘭州常書鴻家作畫(旁
為蔡鶴汀)
石魯的當家絕活是山水畫,也畫人物和花鳥,花鳥畫中的荷花見其獨特的筆意,順勢而為,美不勝收。
—陳莊硯邊閒話
上世紀60年代,石魯很少創作花鳥畫。但上世紀70年代,石魯花鳥畫數量卻很大,成為後期繪畫藝術的重要部分。由於
其形式和題材內容與傳統文人畫相似,但精神上卻又有本質不同,從而被人稱為「新文人畫」。石魯認為:「文人畫是中國
傳統繪畫的一個主流。所謂主流,就因為文人差不多都是用筆墨來表現他們思想情感和個性的。」昔日的文人雅士借物以寫
個人心境,或憤世嫉俗,或孤寂悲涼,或清高淡泊。石魯採用這種形式,是否也有類似的心境呢?從他的諸多作品中,我們
看到的是類似中卻包含著本質區別。石魯也畫梅蘭竹菊荷花,但他不求形似而求意趣,借以詠比抒寫感概。他畫的梅花不是
士大夫文人頌揚的清氣、逸氣,而是「梅為雪而嬌,寒宵更放豪」的豪氣,是「橫掛一枝天地大,不是媚花是梅花」的骨
氣。他畫蘭,筆法金石般厚重拙勁,酷筆粗葉,寥寥幾枝,沒有那麼柔美俊秀,其意不在孤芳自賞詠清高,而是「枯蘭猶
勁笑刀粗」的執拗抗爭,是「蒼宇笑浮華」的冷峻。石魯畫荷,並非追隨「出污泥而不染」的文人畫思維模式,而是以焦墨
濃色一掃脆弱嬌柔之態,畫荷在「雨中紅粉更鮮嬌」,對風風雨雨橫眉側目,是一種不彎不屈的自信,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淡
然。在他的花鳥畫中,沒有昔日失意文人的無病呻吟和自憐,或「墨點無多淚點多」的哀嘆,而是以畫筆「繪事載道,言情
壯志」,更多是對真善美的贊頌。他畫「縱而不顛,奔而信步」的老馬、「月月朝霞如夢」的月季花、五月紅似火的石榴、
「大江大海也趕過」的毛驢、秋江知心的游鴨、春暖桃花從中的村姑。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信手塗抹、養神益壽的玩賞品,
而是發自內心的吶喊,是他道德情操和理想的寄寓。
石魯一生中有兩個創作旺盛期,其中一個在20世紀60年代初,大約是在1960-1963年之間,這是他最初對中國山水畫的探
索期,也是他「野、怪、亂、黑」的起點。第二個高潮就是20世紀70年代,大約是從1971-1976年,這是他文人畫風格的一大
高潮,後來為世人所看重的都是這時所作。至於他在延安時期和20世紀50年代的所作,雖然也有一定的數量,也有一定的影
響,但與這兩個創作旺盛期的作品相比,則要遜色得多了。
從1971-1982年的這10多年中,他的生活也發生了一些曲折。他又兩次住院治療,出院後因問題掛起,暫在家休息。在身
心遭受嚴重摧殘後,他試驗和鍛鍊一下自己的記憶力和作畫能力,又重新提筆,似乎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創作慾望。他每天要
畫兩三幅畫,寫幾幅字,當時約有100多幅,其中荷花特別多,有十幾幅。荷乾挺直,花略施淡紅。通過荷花這種出淤泥而
不染,潔淨而不嫵媚的畫面,寄託作者不媚於俗、我行我素、不屈不撓的倔強性格,這可能是這段時間他愛畫荷花的原因。
石魯創作的荷花多為紅荷,白荷極為罕見。此幅贈白玉龍《白玉荷風圖》,為石魯先生白荷作品中尺幅最大的一件,
花朵以淡色代墨,花莖與荷葉以沒骨之法,純顏色為主,即傳承了中國畫大寫意氣象,又融匯了西洋畫之因素,用筆獨到,
以書法入畫,荷莖穿插錯落,朱砂色的蜻蜓與畫款交相呼應,既有節奏感,又帶朦朧感。由於受迫害,石魯將其用過的大部
分印章磨去,改用筆畫印,根據作品內容與風格不同,畫出不同形狀與佈局的「印章」。此書、此印與畫中的風荷,合成完
美的一體。《白玉荷風圖》作為石魯晚年罕見的巨作,幅愈大而氣愈壯,奔騰奇崛而象中蘊意,既傳遞出風荷的搖曳之美,
更張揚了畫家狂傲不羈、「不屑為奴」的風骨,正是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精神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