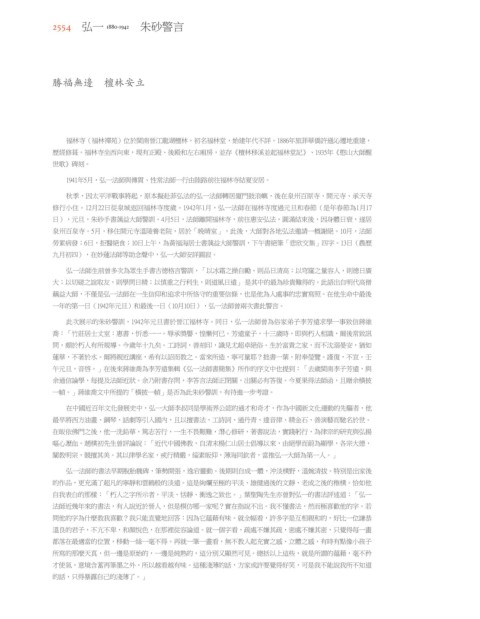Page 224 - 中国书画夜场
P. 224
2554 弘一 1880-1942 朱砂警言
勝福無邊 檀林安立
福林寺(福林禪苑)位於閩南晉江龍湖檀林,初名福林堂,始建年代不詳。1886年旅菲華僑許遜沁遷地重建,
歷經修葺。福林寺坐西向東,現有正殿、後殿和左右廂房,並存《檀林移溪並起福林堂記》、1935年《憨山大師醒
世歌》碑刻。
1941年5月,弘一法師與傳貫、性常法師一行由陸路前往福林寺結夏安居。
秋季,因太平洋戰事將起,原本擬赴菲弘法的弘一法師轉居廈門鼓浪嶼,後在泉州百原寺、開元寺、承天寺
修行小住。12月22日從泉城返回福林寺度歲。1942年1月,弘一法師在福林寺度過元旦和春節(是年春節為1月17
日),元旦,朱砂手書蕅益大師警訓。4月5日,法師離開福林寺,前往惠安弘法,圓滿結束後,因身體日衰,遂居
泉州百泉寺。5月,移住開元寺溫陵養老院,居於「晚晴室」,此後,大師對各地弘法邀請一概謝絕。10月,法師
勞累病發;6日,拒醫絕食;10日上午,為黃福海居士書蕅益大師警訓,下午書絕筆「悲欣交集」四字。13日(農歷
九月初四),在妙蓮法師等助念聲中,弘一大師安詳圓寂。
弘一法師生前曾多次為眾生手書古德格言警訓,「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則德日廣
大;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 是其中的最為珍貴難得的。此語出自明代高僧
藕益大師,不僅是弘一法師在一生信仰和追求中所恪守的重要信條,也是他為人處事的忠實寫照。在他生命中最後
一年的第一日(1942年元旦)和最後一日(10月10日),弘一法師曾兩次書此警言。
此次展示的朱砂警訓,1942年元旦書於晉江福林寺。同日,弘一法師曾為俗家弟子李芳遠求學一事致信蔣維
喬:「竹莊居士丈室:惠書,忻悉一一。辱承獎譽,惶慚何已。芳遠童子,十三歲時,即與朽人相識,爾後常致訊
問,頗於朽人有所規導。今歲年十九矣。工詩詞,善刻印,識見尤超卓絕俗。生於富貴之家,而不沈溺晏安,猶如
蓮華,不著於水。爾將親近講座,希有以詔而教之。當來所造,寧可量耶?拙書一葉,附奉瑩覽。謹復,不宣。壬
午元旦,音啓。」在後來蔣維喬為李芳遠集輯《弘一法師書簡集》所作的序文中也提到:「去歲閩南李子芳遠,與
余通信論學,每提及法師近狀。余乃附書存問,李答言法師正閉關,出關必有答復。今夏果得法師函,且贈余橫披
一幀。」蔣維喬文中所提的「橫披一幀」是否為此朱砂警訓,有待進一步考證。
在中國近百年文化發展史中,弘一大師李叔同是學術界公認的通才和奇才,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他
最早將西方油畫、鋼琴、話劇等引入國內,且以擅書法、工詩詞、通丹青、達音律、精金石、善演藝而馳名於世。
在皈依佛門之後,他一洗鉛華,篤志苦行,一生不畏艱難,潛心修研,著書說法,實踐躬行,為律宗的研究與弘揚
嘔心瀝血。趙樸初先生曾評論說:「近代中國佛教,自清末楊仁山居士倡導以來,由絕學而蔚為顯學,各宗大德,
闡教明宗,競擅其美。其以律學名家,戒行精嚴,緇素皈仰,薄海同欽者,當推弘一大師為第一人。」
弘一法師的書法早期脫胎魏碑,筆勢開張,逸宕靈動。後期則自成一體,沖淡樸野,溫婉清拔。特別是出家後
的作品,更充滿了超凡的寧靜和雲鶴般的淡遠。這是絢爛至極的平淡、雄健過後的文靜、老成之後的稚樸。恰如他
自我表白的那樣:「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衝逸之致也。」葉聖陶先生亦曾對弘一的書法評述道:「弘一
法師近幾年來的書法,有人說近於晉人,但是模仿哪一家呢?實在指說不出。我不懂書法,然而極喜歡他的字。若
問他的字為什麼教我喜歡?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為它藴藉有味。就全幅看,許多字是互相親和的,好比一位謙恭
溫良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裡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畫
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移動一絲一毫不得。再就一筆一畫看,無不教人起充實之感、立體之感,有時有點像小孩子
所寫的那麼天真,但一邊是原始的,一邊是純熟的,這分別又顯然可見。總括以上這些,就是所謂的藴藉,毫不矜
才使氣,意境含蓄再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這種淺薄的話,方家或許要覺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說我所不知道
的話,只得暴露自己的淺薄了。」